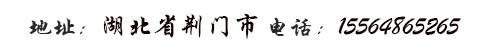随笔食在兖州府
|
食在兖州府(随笔) 邵云虎 食之有味,味中有道;善守其道,源远流长。形端表正、恪守诚信的兖州人没有让地道的美食成为过去,而是永久留在了人们的舌尖。兖州的主食是面食,单调、纯洁的面粉在聪明的兖州人手中,经过烤、烙、蒸、煎、炸、拉、煮等精心制作,变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一方美食,勤劳的兖州人把滋味的传承,留在了幸福的舌尖记忆中。食客在变,味道不变,一方美食在父传子、母传女、师傅传弟子的传承中坚守下来。兖州大烧饼久负盛名的兖州大烧饼已列入"非遗"文化目录可谓名至实归,正宗的兖州大烧饼讲究一大、二香、三无馅,这是和其他地方烧饼相区别的关键。烧饼大近一尺,和面之时加入了葱末、椒盐、食盐、植物油,入炉烤制时面坯内圈涂抹了一层麦芽糖水,粘沾住点撒的芝麻粒,凑成了谐美之"五香"。新疆的馕也大,可兖州大烧饼却没有它那般厚实,河间驴肉火烧吃的是驴肉,包裹驴肉的小火烧不过是一个夹饼而已,有好事者称之为中国的"汉堡哥"!兖州大烧饼仿佛穹顶模样,厚实的边缘象征着圆圆的天边,中间稍薄一些的部分象征着浩瀚的天空,点点芝麻不正象征着灿烂的群星吗?最早的发明者是否联想到"天人合一"思想才会如此设计呢?孩子们爱吃中间的部分,有甜味、有香味,芝麻粘在嘴唇上用舌头舔舐一下,颇有童趣。大人们爱吃的是厚实的边缘,有韧性、有嚼头,咀嚼中体会着麦香原滋味,想到的是沉甸甸麦穗相互挤压碰撞的丰收景象。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地处华北平原的兖州一直以来属于农耕文明,冬小麦是主要农作物和食材来源,高蛋白的小麦给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兖州人荷锄挥镰的能量,相较于玉米而言,兖州人更喜欢小麦的醇厚。经过炉火加工的大烧饼不易变质,即使三伏天也能保存三两天,一大早,兖州人把十几个大烧饼装在包袱里带到田间地头,晌午吃饭时,便取出本身具备五香的大烧饼,不用添加菜肴便能轻松送入自己的肠胃,如果再来一根大葱或一块咸菜就能大快朵颐,无怪乎大烧饼会成为劳动者不可或缺的至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文明渐行渐远,幸福的兖州人不再把大烧饼当做藉以果腹的干粮,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美食。兖州大烧饼成为美食的策略有二,一是增加花色品种,二是为它寻找最佳搭配。增加花色最简单,无非是添加各种馅料,有荤有素,变成了菜火烧,加点糖不就是大糖火烧了吗?为大烧饼寻找最佳搭配的遐思妙想让世人见证着兖州人聪慧的头脑,简单得很,卷上葱段和生菜等变成了"巨无霸"春饼,加上几片猪头肉变成"另类"汉堡……大烧饼是无所不能包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兖州人做不到。好马配好鞍,其实和大烧饼最配的当属油条,兖州的油条个大体胖而酥脆,出锅后不塌不软,如士兵般昂首挺胸,这与外地半睡半醒的油条有着天壤之别。炸油条的师傅若看食客拿着大烧饼而来,他会让油条在油锅里多呆十几秒,色泽如酱时才捞出,这时的油条焦脆挺拔,食客拿上油条拦腰掰成两段并列卷入对折好的大烧饼之中,双手合拢,然后大口嚼之,油条的脆、芝麻的香、麦芽糖的甜、椒盐的咸、葱花的辛辣等自然融合成一首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味觉"交香曲",兖州大烧饼得以广泛流传和这种吃法有着直接关系,日子穷困的时期,烧饼和油条配伍在一起,还成为兖州人走亲串朋的一色礼物。无肉不欢的兖州人还把大烧饼搭配上了羊肉汤,清真老铺内,红烧羊肉现称现切,师傅码放在放置碗底,然后冲入清汤,再加些许老汤,点入红油、撒上香菜,泡上原味大烧饼,这滋味与西安的羊肉泡馍真是难分伯仲,兖州大烧饼是发面制成,比之泡馍更利于消化,所以"羊汤泡烧饼"可谓老少皆宜。兖州大烧饼成为"非遗"文化品牌,而成为"非遗"的产品通常具有脆弱的生命力,不免让人担忧着,但我想,兖州大烧饼就在兖州人日常生活中,依旧是许多兖州人的最爱,它绝不会步入消亡的行列,同样,厚实的壮馍,朴实的煎饼、发面饼、单饼也永远不会消失匿迹。远行的兖州人倍加眷恋家乡的老滋味,耄耋之年的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原籍兖州东关,身在省城的他乡音未改,对家乡的美食念念不忘,这源自于他儿时的舌尖记忆,听家乡来客说,他所熟悉的美食大多数还在,倍感欣慰的他表示一定抽空回家乡大快朵颐,我想,回到兖州的他一定会先买上几个大烧饼,然后卷上酥脆的油条大嚼之,而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不糊不香的糊粥糊粥盛行于兖州已不知多少年,糊粥色黄中带白,呈半固态状,甚为浓稠,嗅之,一股米香、豆香扑鼻而来,入口略有糊味,故称"糊"粥,兖州人吃早点就好这一口不糊不香的糊粥。北京人爱喝入口甚怪的豆汁儿,酸涩苦馊仿佛馊坏,外地人怎么也喝不出甘饴之味,而兖州糊粥对初尝者却没有捏着鼻子硬灌之感,第一口稍觉得有点糊焦之味,而舌后根已有香味冲抵,再喝一口便觉得味道醇厚诱人,顿时顺口,一碗喝完还有"复习"一碗的冲动。我的发小张强是从他师傅那里学来的招数,糊粥里面添加了大米这一南方特产,白天时他挑去烂米、坏豆,然后把大米、小米和大豆洗净后,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时加上水打成沫子放置一边待用,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后,铁锅加水大火烧开,这时投入打好的沫子使劲搅拌均匀,在似开锅未开锅之际撤去底火,用余温将粥顶开,此后不再搅拌,锅底自然而生一层锅巴,锅巴的糊味蔓延到整锅粥中自然有一股糊味,火大糊味重,则汤苦,火小糊味欠缺,则味淡,用劈柴做燃料最易控制火候并使粥品温润。掌握撤火的时机最是学问,张强跟师傅学习的就是这一个技术,悟性差的好几年也不得要领,而伶伶俐俐的人看似明白,可实践起来却常常糊味太重,整锅粥报废,张强学艺三年才出师,自己又干了近二十年,轻轻松松的把糊粥的糊味做到了恰到好处,所以每天顾客盈,不到九点钟几大缸糊粥就已经告罄。糊粥转碗顺沿而喝,喝最上面时觉得不热,然而内部很烫,所以心急的人喝不得热粥,糊粥当是"慢生活"的雅好。转圈喝完后空碗倒置无一点残渣,这就是俗称的"不挂碗","浓如酱,喝似水,喝净粥,碗如洗"的糊粥,滑润爽口,浸人心脾,还能缓解疲劳,增加体能。喝糊粥的标配是撒子或者油条,富足的生活给了糊粥更多的营养搭配,可以泡上切好的羊肉,盛一碟煮好的五香黄豆、细细如丝豆腐皮,再来几根"老虎菜"(咸菜),这一顿早餐是不是够奢侈了?兖州粥铺中经营的不止糊粥一味,大多备有豆汁儿和辣汤供食客自由选择,糊粥和豆汁儿讲究的是味道纯正,而辣汤却强调营养全面,可谓"十全大补",花生米、豆腐丝、海带、面筋、小青菜等结伴于一碗中,再添加姜末、胡椒除湿祛风,一勺陈醋开胃健脾,冬日来一碗,浑身暖洋洋,不啻是严寒天气的首选。老味干饭锅兖州干饭锅闻名鲁西南,位于原酒仙桥附近"孔家"干饭锅可谓翘楚,店主是一个长满络腮胡子飘然在胸的老头,因为慈眉善目的形象太有亲和力,兖州最早的"向阳"照相馆曾专门为他照了一张艺术照,悬挂橱窗内广而告之,那时凡是来城内照相的人无不领略其风采,相互打听着这人是谁啊?故而其知名度特别高。"孔家"干饭锅最先在酒仙桥北,靠着通往金口坝的护城河的河沿上,但随着旧城改造不断地迁移,但不论开在哪里,上午不到十点便挡客于外,老孔说:"卖完了!"慕名而来之人误过这个时辰,可明明看见还有十几碗米饭在案,锅里还有热腾腾的菜,便心生怨谩地说:"那不是吗?"老孔笑吟吟地说:"昨天老顾客的预定,我要给人家留着!"干饭锅讲究老汤煮肉,在兖州就数"孔家"的老汤最老,在他接手之前已有几十年历史,再加上他的岁数,可想而知味道醇厚到什么程度!和兖州干饭锅一样,"孔家"干饭锅里面的菜品也少不了带皮五花大肉块、狮子头、卷煎、炸豆腐、豆腐皮、卤鸡蛋。长时间慢火熬煮,五花肉的油脂化入了老汤,故而肥而不腻;卷煎和狮子头鲜肉剁馅、手工打制,成形后顺入温油轻炸,入锅不散不断;炸豆腐是先把白豆腐切成厚度一厘米半的方块,先在热油锅中炸透成为金黄色,然后几十片叠放在锅中一侧,充分吸收老汤滋味后无滋无味的炸豆腐便有了肉汤的滋味,白豆腐因为炸成固定的形状,故而不会满锅飞,越煮越香。大胡子老孔购买食材最讲究的是"掐尖",市场上的大小商贩包括偶来赶集的乡村菜农都知道他的脾性,他不在乎的是价格,而是质量品质,所以大家争着把最好的东西加上合理的价钱给他留着,一个老菜贩打趣说:"老孔哥,土豆切开还不是一样吗?"他笑着说:"不一样!俊俏的模样惹人爱。"只见他挑的土豆那真是大小一匀、芽坑最少。酒仙桥附近历来商贾云集且又是过去农贸物质交流大会的设立点,所以兖州干饭锅多集中那里。这里还有一家"袁记"最与众不同的是经常歇业,人家竟然任性到常一歇半个月,具体原因不详,我想,店家是不是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中庸思想,让客人的舌尖清除一段时间的美味缓存呢?歇业之后再开门,顾客照样爆满,生意做到如此程度,才是人家敢于浪费高昂房租空置门面的底气。小时代的“奢侈品”——煎包和葱油饼贫穷的童年生活让六零、七零后两代人的味蕾如同沙漠般贫瘠,偶尔的饱饫烹宰经历使他们像"骆驼"一样储存起来,时常用美好的回味滋养匮乏的肠胃。七食堂的煎包和奶奶做的葱油饼永久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它们满足了一个儿童对"吃"的纯真渴望。七食堂的煎包肚大腰圆、两面金黄、皮薄馅多,当时讲究的是一斤馅一斤面,一斤20个,按斤不按个,面、馅都要过秤,足斤足两、童叟无欺。煎包的馅料只有韭菜粉条一种,粉条用以调味,煎包熟后韭菜还是翠绿如鲜。现吃装盘,如翼翅般黄澄澄的金边不塌不断,一咬咔嘣脆,带走则用荷叶包裹,一股浓浓的清香沁人心脾。后来,国营七食堂破产,从里面出来自谋职业的高级技工却把手艺发扬光大,争相增加馅料种类,吸引不同口味的食客。我的煎包记忆来自于父亲的一个"特权",当时父亲是东关大队的大队长,每到麦收季节,父亲都要率领社员们囤场晒粮,最先运到场院晾晒的是"公粮",等到日上三竿,队员们七手八脚把干透到牙齿都无法撼动的小麦装到统一的麻袋装到拖拉机上,父亲和几个队领导亲自押送到粮所。每逢交"公粮"时,各个生产队都会集中而来,等上一天交上很正常,生产队中午管一顿"公饭",饭就是酒仙桥七食堂的煎包。回来时,他拿出用荷叶包着的几个煎包给我,那是他从自己份例中节省下来的。对于每天以玉米面、白面混杂在一起蒸制的馒头为主食的我,这几个煎包无异于山珍海味。我知道要交公粮时,总会守在场院边"监视"每一个环节何时完成,然后是漫长的等待。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在中午前赶回来,那样,我将会失去馋人的煎包。有一次,我偷偷爬到拖拉机上跟着大人们去交"公粮",只见不计其数的马车、牛车、地排车等交粮运输工具挤满了整条大路,许多远路而来的农民还在路上搭起了窝棚。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父亲的"特权"——七食堂煎包飞不了!油料凭票供应的年代,葱油饼这种耗费大量油脂的面食不是随时可以吃到,原料其实简单到只有面、油和葱花还有一点点盐粒而已,可是白面属于年节的专用品,油更是奇缺到用小勺和筷子来把握每次炒菜的用量,能吃上葱油饼是因为奶奶收到了一刀"礼"时,"礼"是一条带有肋骨的猪肉,有肥有瘦,厚厚的膘就是炼油的原材料,炼油后的废渣还会被剁碎包入到水饺中,一点浪费也没有。葱油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和面、醒面,把面团擀成薄薄的面饼,上面抹上一层猪油,然后点撒细盐和葱花,再把面饼卷起来,卷的越紧密成行后的层数越多,卷成长条后又一次把面饼变成面团,再次擀压成一个个圆圆的面坯,这时就可以上锅进行烙制,锅底倒入些许猪油或者豆油,火用小火,最好用麦秸做燃料,当然,现代人早就使用电饼铛之类的加工工具,不过,我还是对奶奶烧制麦秸做成的葱油饼情有独钟,原生态的传统手艺必然有他存在的价值。十几分钟后,葱油饼出锅,奶奶把圆饼横竖两刀分成四份,每个孩子只有一份的量,这一角饼香味四溢,层次虽分明但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层,无怪乎被人称之为"千层饼",一口咬下去,便足以让积存很长时间的玉米面窝头黯然失色,这一角吃完后,另一张饼还在锅中,垂涎欲滴地我盼望它早一点熟透,而奶奶却耐心地不时翻着,让它两面黄澄澄、油光满面。我想,只有这样的食品在"食为天"的物质文明中更具诱惑力,现在,葱油饼天天可以做、可以买,然而,再也勾不起我的强烈食欲,于是,期待着找一个乡间庭院,按照奶奶的技艺亲手做一张葱油饼,温故一下往日的舌尖记忆。作者简介:邵云虎,任教于济宁市兖州区军民学校。近年在《中国青年》、《人生》等杂志发表篇散文、随笔。编 后当年如果不是津浦铁路途经兖州城,并设立“兖州府火车站”,兖州不过是鲁西南平原上的一座灰尘飞扬的“土城”。想当初,火车隆隆驶来的景象:汽笛长鸣,车轮铿锵,城中大小教堂,荡起悠扬的钟声,响彻方圆百里,兴隆塔的影子从旅客仰望的窗口渐渐消失。可以这样说,兖州是上世纪之初为数不多的最早步入现代文明的城市之一,中山路上商铺林立,府河左右餐馆飘香。时过境迁,而今兖州,除了“兖州府”这个名称可以提及之外,其它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了。我在这个小城生活已有几十年了,但要说起兖州的“吃”来,我还真说不出名堂。民以食为天,邵云虎记叙的这些所谓“美食”,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必须的食品,烧饼,糊粥,干饭,包子,油饼,哪样不是居家必备。但在那些饥饿的年月,却是垂涎欲滴的“美食”。 孔夫子言,“食不厌精”。精到什么地步,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对食物的想象肯定考验人的语言功力。就说李白居家兖州的那些年吧——这个著名的吃货,单凭诗才就能吃遍全国,也吃遍兖州府郡周边的城镇,蒙山吃过,徂徕山吃过,任城、金乡、汶上等县城统统吃过,有诗为证:“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兰陵美酒郁金香”“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可见美食之于诗歌,那是无中生有,锦上添花。 文学作品中的美食不是菜谱。对“吃”的描绘,多半是添油加醋,绘声绘色。若照红楼梦里描写的美味佳肴做一桌大餐,无异于将文学人物对号入座,那是愚蠢之行。美食在民间,好吃的不是土中生,就是水中养,飞禽走兽,山珍海味……舌尖上的美味大多是来自对饥饿的记忆。(王黎明)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ihaibao.com/lshbzqxz/8285.html
- 上一篇文章: 山东各地美食特产美酒
- 下一篇文章: 紧急通知兖州改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