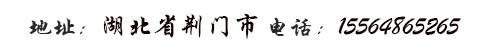1980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对谈
|
菲利普·罗斯与米兰·昆德拉对谈录 中译:陈婉容编辑:Piking 此访谈是我拜读过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的译稿后,与他两次进行对谈的浓缩内容——一次是他首度到访伦敦的时候,另一次则在他初访美国时进行。他这两次旅程的起点都是法国;自年起,他与妻子便以流亡者的身份居住在雷恩,并于当地大学任教。现在他们搬到巴黎了。我们对谈的时候,昆德拉偶尔会讲法语,不过主要还是说捷克语。他的妻子维拉负责为我俩翻译。彼得·库西将最终版的捷克文稿译成英语。 罗斯:你认为世界很快就会毁灭了吗? 昆德拉:那得视你如何定义很快这个词。 罗斯:明天或后天。 昆德拉:世界正急速毁灭的看法自古有之。 罗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昆德拉:正好相反。一种恐惧能始终长存于人心,自然有它的道理。 罗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新作中的所有故事似乎是以这种担忧为背景而展开的,就连那些明显属于幽默调性的故事也是。 昆德拉:如果有人在我小时候对我说,“终有一天,你会看见你的国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会觉得那是无稽之谈,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事。人人都晓得自己终有一死,但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必会千秋万世。然而年俄军进犯捷克后,每位捷克子民都不得不这么想:我的国家可能就无声无息地从欧洲消失了,一如过去五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四千万名乌克兰人无声息地从世上消失一样。立陶宛人也有类似遭遇。你知道吗,17世纪的立陶宛可是欧洲强国,而如今,俄罗斯人将立陶宛人像半灭绝的部落一般圈限在保留区之内;为了防止外界知道立陶宛人还存在,俄罗斯人把他们封锁起来、谢绝所有访客。我不晓得我的国家未来将发生什么变故,不过俄罗斯人肯定会竭尽所能地将它逐渐吞没进他们的文明里。天知道他们能否如愿以偿,但确实有可能。而突然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便足以让一个人对生命的全面观感产生变化。现在,就算是欧洲,我都觉得它不堪一击、无法长久于世。 (PhilipRoth) 罗斯:不过,东欧与西欧的命运天差地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吧? 昆德拉:从文化史的观念来看,东欧就是俄罗斯,因为其历史扎根于拜占庭世界。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则和奥地利一样,从不属于东欧的一部分。打从一开始,这些国家便参与了西方文明伟大的冒险,如哥特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以此为发源地。也是在中欧这个地区,现代文化得到了最强劲的脉动,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十二音列作曲法、巴尔托克音乐、卡夫卡和穆齐尔的小说新美学等。而战后俄罗斯吞并中欧(或至少是中欧的主要部分),则导致西方文化失去原本的重镇。这是本世纪西方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此我们不能否定中欧的末日即标志着整个欧洲步向灭亡的可能。 罗斯:在“布拉格之春”运动期间,你的小说《玩笑》和短篇集《好笑的爱》出版了十五万本。俄军占领之后,你在电影学院的教职被撤,所有作品也从公共图书馆的架位上给撤了下来。七年之后,你与妻子将几本书和几套衣服往后车厢一扔,驱车开往让你跻身为最多人阅读的外国作家之列的法国。作为一个流亡者,你有何感想? 昆德拉: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在许多国家生活过的经验是一种无上的恩惠。不从多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话,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我最近在法国出版的《笑忘录》就是在一种特别的地理空间里开展:透过西欧人的眼来看发生于布拉格的事件,而发生于法国的事情,则透过布拉格的眼来审视。两个世界间在此邂逅。这一头是我的祖国:仅仅半个世纪,就历经民主政体、法西斯主义、革命、斯大林恐怖肃清,还有斯大林政权的解体、德国与俄军的占领、驱逐出境的大潮,以及西方在自家土地上的败亡。于是,捷克被历史的重量压得向下沉沦,致使它以极度怀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而另一头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处于世界的中心,至今却苦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匮乏,所以陶醉在激进意识形态的姿态里。这是一种对自身有所作为的期待、充满感情却过分焦虑的期待,然而这种期待还未实现,也永远不会实现。 罗斯:你是一个住在法国的异乡人?或觉得自己在文化上如鱼得水? 昆德拉:我热爱法国文化,且深深受惠于兹——特别是旧时的文学。我最珍爱的作家是拉伯雷。还有狄德罗,他的《宿命论者雅克》就像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一样令我爱不释手。他们是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小说形式实验家。他们的实验可谓非常有趣,充满了幸福与欢乐,而这在今日法国文学中已不多见。少了这种有趣的实验,艺术就失去意义了。斯特恩和狄德罗把小说理解为一种伟大的游戏,因为他们发现了小说形式中的幽默。听见小说业已穷尽所有可能的学术论点时,我倒有种完全相反的想法: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与许多可能失之交臂。举个例子,斯特恩和狄德罗的作品蕴藏着刺激小说发展的推动力,却未有任何后继者接替这股动力。 (MilanKundera) 罗斯:《笑忘录》没被归类为小说,但你在文中宣称此书是一本变奏形式的小说。所以它究竟是不是小说? 昆德拉:就我非常个人的美学判准,它确实是部小说,不过我无意将我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人。小说形式潜藏巨大的自由,若将某种已定型的结构视为小说不容侵犯的本质,就是一种错误。 罗斯:但是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自然有它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也必然限制了你说的自由。 昆德拉:小说是长篇的合成性散文,建立于虚构人物的活动之上。这就是唯一的限制。我用“合成”这一词,因为想到小说家欲从各个方面掌握自己的题材,并尽可能将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渴望。讽喻性散文、小说式叙述、自传性的断片、史实、天马行空的想象——小说的合成力量能够将各种元素合为一体,有如结合多条旋律的复调音乐。一本书的统一性不需仰赖情节而生,可以由主题获得。我的新作中就有两种这样的主题:笑与忘。 罗斯:笑与你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透过幽默或反讽手法,你的书激发了读者的欢笑。书中人物会遭遇不测,是因为他们碰撞上已经失去幽默感的世界。 昆德拉:我在斯大林恐怖肃清时期学会了幽默的价值。当时二十岁的我,就能从一个人的笑容辨识谁并非斯大林主义者、谁不是我需要畏惧的人。幽默感是种可靠的辨识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对毫无幽默感的世界感到恐惧。 罗斯:《笑忘录》还包括其他内容。你在一则小寓言里比较了天使的笑和魔鬼的笑。魔鬼笑了,因为他觉得上帝创造的世界毫无意义;天使愉悦地笑了,因为在上帝的世界中,万物皆有意义。 昆德拉:是呀。人类用同一种生理展现方式,也就是笑,来表达两种不同的形而上态度。某人的帽子掉进新坟里的棺柩上,这个时候葬礼便失去了意义,笑声油然四起。一对爱侣手牵着手奔向草地的另一头,发出阵阵欢笑。他们的笑与笑话、幽默都无关,那是他们展现存在的快乐而发出的严肃天使之笑。这两种笑都是对生命感到愉悦的笑,但若过于极端,就会显示双重的天启:天使之笑的狂热拥护者是如此深信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随时准备将不愿意同乐的人吊死。而从另一头传来的笑声在说一切都已了无意义啦,连葬礼这种场合都变得荒谬可笑啦,集体性交也不过是滑稽的默剧演出。人类的生活受制于两股分歧的约束力:一边是狂热,一边是绝对的怀疑。 罗斯:你现在说的天使之笑,即是你以前在小说中提到的“对生活的抒情态度”。你其中一部作品就将斯大林恐怖肃清时期描绘成绞刑刽子手和诗人的统治时期。 昆德拉:极权主义是个水深火热的地狱,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乐土——一个人人和谐共存、拥有同一种共识与信念、没有任何秘密的古老梦想。安德烈·布勒东谈到他渴望居住的玻璃屋时,也曾向往这种天堂。这些美好原型深埋于我们所有人心中,也植根于所有的宗教,要是极权主义没有将之挖掘出来利用,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与极权主义同声相应了,尤其在它尚处初现阶段的时候。然而,一旦人们梦寐以求的天堂开始转变为现实,便会有人现身铲除碍事者,导致这片天堂的统治者必须在伊甸园边建造一座小小的劳改营。久而久之,这座劳改营变得更大、更完善,与之毗邻的天堂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贫乏。 罗斯:你书中提到伟大的法国诗人艾吕雅在天堂与劳改营的上空翱翔、欢唱。真有这一段历史吗? 昆德拉:保罗·艾吕雅在战后舍弃了超现实主义,转而大力鼓吹我可能称作“极权主义诗歌”的东西,成了最重要的倡导者。他歌颂友爱、和平、正义、更加美好的未来,称颂袍泽之谊、反对孤立;他高唱欢乐,反对阴郁,也为天真而歌,要人摒弃愤世嫉俗的观念。年,艾吕雅一位布拉格的超现实主义友人扎维斯·卡兰达拉遭天堂的统治者判处绞刑,他为了更高的理想压抑了私人的友谊情感,并且声明赞同朋友被处决的立场。刽子手便在诗人的歌声中绞决卡兰达拉。 还不仅止于诗人。整个斯大林恐怖肃清时期即是集体抒怀谵妄的年代。这事至今已完全被人遗忘,但正是问题的症结。人们总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革命很美好,只有由革命而生的恐怖才邪恶。其实并非如此。邪恶早存在于美好之中,地狱也已包藏在人人想望的天堂里。若想理解地狱的本质,就从它的渊源——天堂的本质去审视。厉声挞伐劳改营何其容易,但要否定取道于天堂、导致劳改营生成的极权主义诗歌却依然困难。今日世人明确地拒斥劳改营,但他们仍乐于受极权主义的诗歌蛊惑,乐于在卡兰达拉的尸体化作一缕青烟、从火葬场的烟囱升往天际时,听着翱翔于布拉格上空的艾吕雅宛如手持里拉琴的大天使般,高声弹奏同一首抒情曲,并随着歌曲的旋律迈向新的劳改营。 罗斯:你散文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公与私持续不止的冲撞。但那并非指私人情事以政治事件为发生背景,也不代表政治事件干预了私人的生活。你不断说明政治事件与私人情事同为某种规则宰制,也因此,你的散文是一种对政治的精神分析。 昆德拉:不管在私领域还是公领域,人类的形而上学都呈现相同的内容。就拿这本书另一项主题“忘”来说好了。死亡即是自我的消亡,这是人类在私领域中的大哉问。但什么是自我?自我是我们记忆所及的一切的总和。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会丧失未来才惧怕死亡,而是因为我们将丧失过往。遗忘是存在于生命中的一种死亡形式,而这就是我书中女主角的难题:她拼死想保有对挚爱亡夫那正在消逝的记忆。遗忘同样也是政治上的一大问题。一个强权大国想要剥夺某个小国家的民族意识时,就会采用计划性遗忘的手段,这正是波斯米亚地区目前经历的。十二年了,具有任何价值的当代捷克文学作品都没有付梓出版,先后遭禁的作家多达两百位,包括死去的弗朗茨·卡夫卡。一百四十五位捷克历史学家被解雇,历史被篡改、纪念碑被拆毁。一个国家若无法认识自己的过去,就会逐渐丧失自我。因此,政治情势也以残酷的方式阐释我们无形中时时刻刻面对着的遗忘,这个平常的形而上问题。政治揭露私人生活的形而上问题,私人生活也揭露政治的形而上问题。 罗斯:你这本变奏式小说到了第六部分,女主角塔米娜来到一座岛屿。岛上只有孩童,而这些孩童最后将她追逼至死。这是一场梦境、一篇童话,还是一则寓言? 昆德拉:最与我格格不入的就是寓言了,那是作家为了阐明某种论点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不管事件是真实也好、虚构也好,事件本身都必须具有重大意义,读者本当天真地给事件的力量和诗意诱惑。有个影像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之中,有段时期,它老浮现在我的梦境里:有一个人发现自己身处儿童的世界,无法逃脱。突然之间,我们咏叹、热爱的童年生活变成纯粹的恐怖,以及一种圈套。这篇故事不是寓言,不过我的书是一曲复调,以不同的故事互为说明、阐发及补述。这本书主要在讲极权主义的事件,描述极权主义借由剥夺人们的记忆,将他们全改造成儿童国民。这是所有极权主义的一贯作风。或许整个膜拜未来、膜拜青春与童稚,对过去漠然、对思维存疑的科技时代也这么做了。在一个幼稚到无可救药的社会里,拥有记忆、能够讽刺的成年人就跟在儿童岛上的塔米娜没什么两样。 罗斯:你全部的小说几乎都以性交场景作结——尤其在你的新作中,每一部分的故事都是如此收场。甚至以“母亲”这个纯真之名为标题的第二部分,也不过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长篇三人性交场景。以你小说家的身份来看,性有何意义? 昆德拉:这个时代的性已不再是禁忌,仅仅描写性事或性欲的告白也明显令人感到乏味了。劳伦斯的作品读来多么老派!甚至亨利·米勒以抒情手法描绘的淫秽场景也已过时了!但我始终记得乔治·巴代伊笔下某些情色的段落。或许是因为那些段落并非只重情感,还饶富哲理。你说得对,我的作品都是以情色场景结束。我觉得交媾场景能引发一段炽烈的光,一下便将人物的本质给映照出来,并为他们生命的情境做出总结。和雨果做爱的时候,塔米娜拼命想要唤醒她与亡夫共度那些假期的回忆。那个情欲场景汇聚了故事所有的主题及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罗斯:最后的第七部分其实只在探讨性。为什么要以这部分作为全书的最终章,而不用别的部分,例如女主角死亡这种戏剧效果更强的第六部分来结尾? 昆德拉:从隐喻上来说,塔米娜是在天使的欢笑中死去的。另一方面,书的最后一部分回荡着某种迥异的笑,就是事情失去意义时我们会听到的笑声。有一条假想的界限,而界限之外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荒唐可笑。有人自问:要我早上起床不是很没意义吗?为了去工作?为了去争取些什么?为了去融入这个国家?只因我生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子民?人们距离这条界限仅有数步之遥,很容易就发现自己已身在界限之外。那条界限随处皆有,它就在人生各个领域里,甚至在最深沉、最生物机能的性之中。也正因为性是生命里最深沉的区块,其引起的疑问就会是最深沉的疑问。这便是为何我那本变奏式小说会以这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结束。 罗斯:那么,这是你极致的悲观表现吗? 昆德拉:对于悲观与乐观这两个词,我认为还是小心为妙。小说不会坚称什么,它做的就是探索和丢出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国家会不会消亡,也不知道我故事中哪一个人物说的话是对的。我创造故事,让它们互为对照,并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人们的愚蠢在于为事事提供答案,小说的智慧则在于为事事提出质疑。当堂吉诃德离家去见见世面,那个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一个难解的谜。那是第一部欧洲小说留予后世小说史的遗产。小说家教育读者将世界理解为一个问题,而这种态度包含了智慧与宽容。以不容变更的定则建立起来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存在。建立于马克思主义、伊斯兰教或是其他立足点之上的极权主义世界,都是充满答案而非问题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不适合小说。总之在我看来,当今世人似乎宁愿判断而不去理解、宁愿回答而不去提问,于是小说的声音就这么被人类定则的嘈杂愚声淹没。 (MilanKunderaVeronicaGengPhilipRoth) 选自:《行话:与名家谈文学》 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年版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至英文原稿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ihaibao.com/lshbzqxz/459.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绿河大学副校长罗斯詹宁斯来我院参观调
- 下一篇文章: 同样是卖资产,李嘉诚一栋卖402亿,王健